
伊斯兰教缺乏神学资源可以帮助他们看待政教关系,伊斯兰基要主义认为,《可兰经》里的宗教法不区分律法的神学基础和它的道德政治基础,因此国家立法,并将律法应用于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常态,教会和政府之间很难有一条界线。这就不难理解现今的伊斯兰国为什么发动恐怖袭击,试图毁灭异教徒,建立一个伊斯兰律法世界。
文/(美)卡森 译者:李晋 马丽 编辑:罗曼
需要认识到的重要一点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具备丰富的神学资源,来帮助人们用符合《圣经》的方式思考这些事物。这些资源包括耶稣的名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可福音12∶17;约翰福音18∶36),以及一些有原则的张力:在相信基督徒需因上帝设立政府而顺服之(罗马书13∶1—7)和相信有时政府是一个逼迫人的怪兽(如启示录13∶19)之间;在相信《圣经》教导人要为这城求平安、富足(耶利米书29∶7),和相信《圣经》说信徒会遇到逼迫(约翰福音15∶18—16∶4;启示录13∶7)之间。而且,基督徒常基于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就要求人可以被公平对待。还有,基督徒坚持认为唯有圣灵能让人重生的真理,唯有圣灵有能力照亮人心、让人归信,而对于国家强制的禁令,最多只能塑造外在行为的统一,而非重生。这些问题很复杂,但对于政教分离,我还有三点思考,作为对第一层面的结语。
(1)某种程度上,基督教信仰一直在和政教关系角力,这不仅仅是因为来自《圣经》的一些教导。当然,在教会历史的前三个世纪中,基督徒是罗马帝国中的少数群体,也常常是一个被逼迫的群体。但是,就连在君士坦丁归信之后,主教们也有时会抨击皇帝(如第四世纪时,安波罗修[Ambrose]曾斥责过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中世纪期间,教皇和君主之间相互负责的关系提醒我们,权力并非只在某一个领域中。所有人都承认,在第七世纪之后,基督徒对政教关系的反思,远远多于早期几个世纪。但尽管如此,教会历史提醒我们,圣经中本已经提出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差异,不仅在欧洲,在各地都存在,而基督徒会一直处于这种张力之下。在最基本的层面,我们想到上帝子民在旧约中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民族,即以色列民族;而到了新约时期,上帝子民的位置,并非一个民族,而是教会,一个信徒组成的国际性群体,并非被任何一个国家所限。
(2)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均衡是一直显明或协商好的。很多美国人觉得,政教关系这个俗语是嵌入美国宪法中的,但这当然不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国会不得指定下列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自由宗教活动,或限制言论自由、媒体出版自由,或干涉人们和平集会的自由、人民向政府和平请愿的自由。”可以讨论的是,修正案提到国会不得“建立国教”,在当时是鉴于很多州已经建立了“国教”:例如,康涅狄格州是和公理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国会不能干涉这些事物。“在教会和政府之间筑起一道墙”这样的修辞第一次出现,是在杰佛逊写给丹伯里的浸信会的一封信中(1802年)。这个说法在1878年(雷诺兹[Reynolds]诉美国政府)被收入最高法院决议的词库中,但直到1947年著名的艾沃森(Everson)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之前,都没怎么发挥出影响力。
但是,很多西方国家中仍设立了官方宗教(如英国、丹麦),这些国家的人们所享受的宗教自由和美国人一样(虽然略有差异),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宽容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时,如一些爱说笑的人所言,法国因为在1789年革命,并没有保障宗教自由(freedomof religion),而是限制了宗教影响自由(freedomfrom religion),这为教会和政府之间造成了很多障碍。
政教关系的不同发展之后果之一(不论好坏),就是宗教不断面临压力,被限制到私人领域,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政府不能建立官方宗教,也不能限制宗教发展;反过来也如此,我们也承认,宗教无权控制政府。那么,一些人更进一步推论说,宗教无权影响任何政府的决策,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宗教应该被限制在一个小的、私人化的世界里,否则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巨大障碍就被破坏了。这样说是跳过了一大步。如果将这一结论贯彻到底的话,我们认为,上千万的民众会在千千万万个方面丧失他们的权利。看起来好似很简单、有益的理想(即教会和政府的分离),会突然被一些广泛被接受的文化假设所充满,对于爱思考的基督徒而言是很难接受的。
(3)如果我们放弃基督徒的假设,进入伊斯兰世界时,关于政教关系的讨论就变得更困难多了。很多人发现,伊斯兰教缺乏神学资源可以帮助人们用新的眼光看待政教关系。例如,那里并没有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可福音12∶17)相似的话。这并不是说伊斯兰世界并未展示过它的宽容。在历史上,一些伊斯兰王权比另一些王权更宽容些。在过去一百五十年左右,少数穆斯林学者认为,重要的圣战(jihad)并非对外在敌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内在的属灵争战。因为一些穆斯林迁徙到了西方国家,在那里,关于宽容的问题在公共讨论中占据了一些空间,所以可以读到一些像伊斯梅尔·阿贾尔写的重要文章《伊斯兰的宗教宽容之神学基础:可兰经的观点》,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看来,这些讨论的奇特之处(正像它们很受欢迎一样)在于,它们从不探讨政教关系。他们会想象敬虔的穆斯林可能怎样在西方生活,他们想起穆斯林国家(可能或应该)怎样以恩慈的安拉之名对待少数宗教团体。但是他们没有想象过一个教会和一个政府怎样在不同的领域中运作。“在未受到西方对政教分离(对伊斯兰而言,这个问题也许很难讲清楚)的讨论的影响之情况下,伊斯兰基要主义认为,可兰经中的宗教法不将律法的神学基础,和它的道德、政治基础加以区分。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国家立法的正常范式。”
的确,政教分离这个概念,可能对于伊斯兰信徒而言是亵渎性的:18世纪从欧洲发展出来的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是穆斯林思想完全陌生的,就连“教会”的概念,或不同宗派“教会”的概念,对他们也是完全陌生的。真主安拉的子和那些构成穆斯林国家的人民之间,是不容易区分出来的。
伊斯兰的律法被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而真主安拉是容不下竞争对手的。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在教会和政府之间凿出一条界限呢?对于那些从未在西方生活过的穆斯林而言,所谓的“私人化的”宗教,是不太好理解、也不太一致的。在他们看来,那些过着私人化宗教生活的人们也是不吸引人的。在弗吉尼亚州老自治州大学任教的阿赫塔尔曾写过一本非常棒的、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他在书中说到,伊斯兰教最终会(也应该)赢得世界性的主导地位,因为只有伊斯兰教(而非基督教)才是自身具备成为一种帝国性宗教的一支。
当我们了解到如“信仰自由”这样的表述,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具备非常不同的意思时,这里的一点观察的重要性才会更明显。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信仰自由不仅仅假设人们可以在没有阻碍或鼓动之下自由地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假设人们基于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可以自由改信另一种宗教或无宗教;也在公开辩论、信息传播和争论的范围内,可以自由传播他自己的宗教信仰。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第18条:“每个人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可以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自己或在社区中公开地或私下以教导、实践、敬拜、观察等方式向他人表明自己的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简单做一个总结:从约翰·密尔(英国哲学家和公职官员)以来,我们对宽容观之发展的第一点观察是,对宽容和非宽容之本质的各种争论,是围绕着政教分离这个问题展开的,而这个观念是由基督徒从对圣经的研读中提出并为之辩护的。尽管政教分离的观念非常宝贵,却在西方的不同地区逐渐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其中常常指向宗教信仰的私人化;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对这个观念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摘自卡森著《宽容的不宽容》,李晋、马丽译,团结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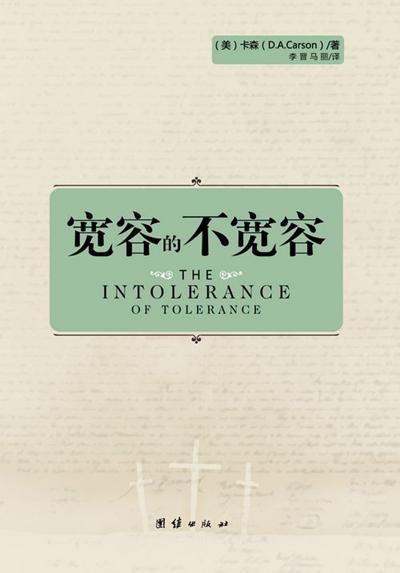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