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资深编辑和名作家之间的片面故事。 张文亮是一位多产的台湾基督徒作家,曾写过《兄弟相爱憾山河》、《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记》等着作。吴鲲生则是台湾校园杂志的资深编辑,多年前经由他鼓励,而有了张文亮的这支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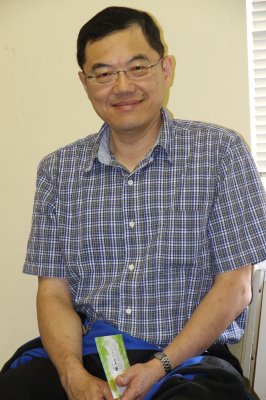
(图左:吴鲲生编辑,右:张文亮教授)
2012年回台,不只带领台湾点燃写作文字火种文字营,也结识了吴鲲生介绍的张文亮。
去和他们两位见面的当天,正好是我两本书出版的日子,因为想带去送他们,于是经历我20多年写作生涯里的第一次,就是在宇宙光出版社八楼的电梯前望穿秋水,等自己出版的书从雨天塞车里被送到。当时林治平林哥也在身边陪着,心中只觉好笑,身在海外,我这作家有太多的例外,得了十多个文学奖,只有一次本人回来领奖,出了十多本书,也只有这是第一次等着书送进出版社。而且,要等送到,才知道书到底长什么样。
结果,书送到了,拿到手也没时间看清楚,就往外跑了。和吴哥约好在台大见,他很体贴地撑着伞等在台大公车站下。随后,更发现吴哥是一个很细心体贴的人,先带我先去台大福利社买午餐,因为张文亮是很不在吃上讲究的人。我们买了两个饭团,台大「超大级」饭团,是我们一般见的叁倍大。
然后去张文亮在台大任教的办公室,一栋有着年纪的楼房底下。在台湾基督教圈里,张文亮算是多产也畅销的作者,最着名的就是《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也曾分享过他所写的《深入非洲叁万里--李文斯顿传记》。等去到他办公室时,就知为何了。他望着走入房间的我们,完全不知那时几点,桌上摊着稿纸,他正在进行下一本书的书写。然后吃中饭时间,他只有一根香蕉。
我便把自己超级大饭团分了一半给他。吴哥也很体贴的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盒切好的水果,芭乐和杨桃,我们就如此地开始餐叙。张文亮是一个学者型,很有些书生气,见到吴哥就嘻嘻笑的拿出一本画册,是他刚画好的一幅铅笔画,一只趴在栏杆上的狗,挺逼真。他说他母亲也会画,我看了几幅(包括最近一期《校园》杂志封底),很有开画展的水准。
我们谈到写作对他的意义,他说写作对他是一个「转化」,他说话很跳跃,也很断裂,但是学识渊博,因此听他说话要很认真,否则精采就会被跳过了。他说自己学的是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当即,送了我一本他写的《圣经与植物》),但因大学受洗时,曾被一位属灵导师毛松霖带过,这人想必是个人物,因为毛告诉年轻的他,真正影响人类的只有叁个领域:历史、经济和文学。并说「历史是探讨时间的函数」(很玄),因此张文亮在科学外又选择了历史,自修研究各类历史,包括音乐史、艺术史、科学史、文学史、宣教史.....这让我忽然发现什么领域都有一个历史,走这个角度来研究,可真是深深掌握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了。
毛带领张文亮到一个程度,就对他和那时的一群学子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要他们离开,包括换教会,换找属灵师傅。看我不解,吴哥便解释说那是表示毛已经传授所有,再下去,张文亮这学生便会超越毛了,因此应该另找老师来传授。真是一个让人求之不得的思想启蒙恩师。
第二个影响张文亮思想的,是那时开往台湾的福音船。在那个时代,台湾资讯有限,尤其来自西方的。福音船却带来大批英文属灵资源的书,在校园书坊里很便宜地卖。张形容自己那时每次是用「麻袋」来装买的书,这些书大大开启了他属灵的思想。后来他出国留学,在UC Davis拿到博士。回国后,就恰好住在吴鲲生家的附近。这是上帝一个巧妙的安排。
因为两个火种如此近,很难不擦撞出火花。张说他曾经历过叁个孩子的流逝,有很多的忧伤。那时吴哥便鼓励他写作。后来张文亮形容写作对他,好比把忧伤的水舀出去的一种方式。
一个多产,有思想深度,写作幅度又跨越很广,什么领域都有可能成书的作者,就在吴哥的鼓励下产生了。吴鲲生说对校园出版社来说,好像得到一个宝,他望着张文亮的笑容,也像是望着一个「宝」。张文亮谈自己,很多也都是吴哥在那补充,真是伯乐与千里马。我想是许多作家的梦吧?能在写作生命中有一个「吴鲲生」。
张文亮是以研究起家,又有文学笔触,很多书名都很长,也都很有诗意,比如《昨夜,我与一颗橘子摔角》、《谁能在马桶上拉小提琴》、《夜在沙滩边等待一只螺睡觉》。他的特点就在能把高深学问深入浅出地写出,而且对孩子很有负担,出过多本科普类童书,多次入选时报好书大家读和儿童及少年图书类金鼎奖。他最新出版的《因为有爱,才有这个学系》,就是为了他教通识课的大一学生,是探讨大学科系的起源。好像只要有一个「问题」,他就可以用「一本书」来作答。
学者身分加上教授身分加上带点诗意的笔,走出一条独特的写作路。书不只在基督教书坊里畅销,也在属世市场里多面打入,信仰融合得特别透和深。一方面因为自己所学,很亲近大自然,各种生物现象都能写入文字。另一方面又亲近人类史,各类科学大师和宣教士传记一一出版。写作天地对他来说,是无限宽广。
但很有意思的是,创文异象「在时代里携手」,对他这样的作者好像便不大适用了。因为他在写作与灵命两面都自给自足,也很荣耀神,个人身体状况又不是太好,想写的太多,时间太有限,能写他有兴趣、有负担的,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好像不再需要和更多的文人结识来作些什么。
从头到尾,我便没机会谈创文,他也没有问,好像也无所谓了。就当认识了一个可贵的作者灵魂。
告别后,吴哥说他再带我走去校园书坊,他要买张文亮最新的书《因为有爱,才有这个学系》送我(张文亮自己都还没有)。随着他在雨天走去时,心中也有些许感动,吴哥是一个谦逊到家的人,而且一生在《校园》杂志社服事,生活极为简朴,标准的打扮是一件浅色夹克,背一个书包,骑车在风雨里来回。因此,每次让他破费都让我很不忍。但凡每个知道吴鲲生的人,都对我说他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思想高度、很能作出一番事的人。但他这个人很纤瘦苍白,像一个影子,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自己,总是:我不能,我不太行,我不.......,完全看不出来「人言」所铸造出的一个属灵人物。我读一些他写的文字,再和眼前这人比较,也老摸不清,这会是同一个人么?
生平第一次了解什么是「虚怀若谷」,很让我摸不清虚实。
校园出版社社长曾经和我说,吴鲲生栽培作者一生,只栽培出了一个张文亮(这成为他们对栽培作者不大抱希望的一个实例)。但这样重量级的作者,不也够了么?后来,我和翻译老师顾美芬见面时,她也提到和吴素昧平生,却在一次分享翻译后,回家没多久,便收到吴鲲生寄来的一个包裹,送她谈翻译的几本书。她说吴鲲生也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喂养过她。
每次见面,吴鲲生也会细心的给我几篇影印文章,完全不露痕迹地文字交流与帮助。我为这样一个忠心为神事奉的文字人感谢神,想想他一生作编辑,自己所写的作品很有限,却会为张文亮的出书成就如此欣然。特意带我去买张的书时,好像是他孩子出的书。在校园书坊付钱时,还会问店员:「这本书有人买么?」店员回:「有的!」他便不自觉地微笑。远在研究室里,又开始埋头苦干写下一本书的张文亮,自然对这一幕毫无所知。
一个作者若能碰到这样的编辑带领和栽培,是何等福气?这种伯乐千里马的关係,又何等美? 为这一对编辑和作者,我感谢神!
当天,吴鲲生又把我带回校园办公室,然后和我「纸上谈兵」,谈香港的几个重点性基督教文字机构和负责人。几天后,在点燃写作火种营会里,他又把我引荐给香港基督教资深文字前辈黎海华。趁讲座中的午餐空档,我和黎海华想要进一步深谈结识时,吴鲲生又递出两盒切好的水果(从他的书包里拿出),然后又退下到别处让我们深谈。一个小小的,却很窝心的体贴。
最后一天营会结束,发证书时,每十个一批到前面。他也从阶梯下来,特意到桌上去找他的证书,然后也和其他学员一起拿着照相。那是一个历史镜头,因为,在场人全都知道他在文字领域的份量和资深,他在《校园》杂志作编辑到退修,近四十年!他在营会里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文字领域里的谦卑和鼓励。「在时代里携手」,在他身上,竟然是用这样一种谦卑的方式呈现!我心中只有感动和感恩!
这是一个让我们敬佩又值得学习的一位文字老将!常和创文同工们勉励,盼我们也能有如此让他人作者兴盛,我们衰微的无私奉献心。求神使用并坚固吴哥手所作的所有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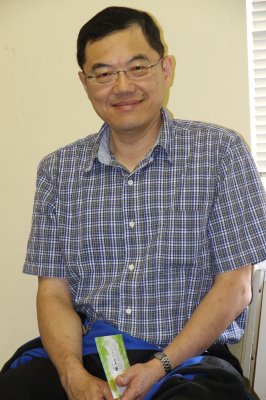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